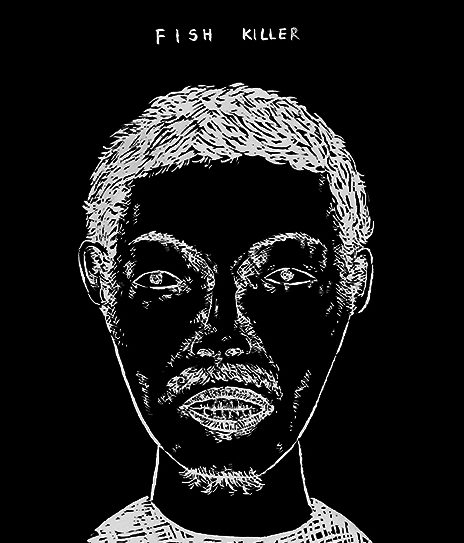我人生絕大部分子日子活在人口稠密的台北市,那在裡人類彼此壓縮在狹小空間之內,呼吸彼此的喘氣。
台北經常下雨,師大路公園的草坪永遠有溼滑的質感,你褲子上總是有個濕淋淋的屁股印子。
在下雨天的星期五晚上,我總是穿過滿是水的巷子,打開咖啡店的門的時候眼前看到的是,在世界末日的盡頭般各自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彼此取暖的人影,角落裡塞滿了已經看過、還沒看過、似曾相似的人們。
但是在這濕漉漉並且擁擠的城市當中,我總是孤獨地感到發慌,在永遠無法躲開人群的狹小巷弄中,在人群裡、你再也無法證實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擁有一樣的長相、一樣的穿著、一樣的時尚、一樣的生活模式,這樣的自己,終究不過是這國家裡橫行各地的青少年大軍的一員,此種想法總是讓我感到從內心而起讓人發狂的孤獨感,
同樣的,我身邊的朋友最常掛在嘴上的字眼,一是孤獨、二是虛無、三是絕望。
週五晚,凌晨的灰白光線在和平東路一帶徘徊,朋友們從地社如地窖般黑暗中爬出,坐在滿是狗屎的師大公園草皮之上,孤獨虛無與絕望這三個字在這群年輕人嘴巴裡環繞著,說著。
在我離開台北的最後一天晚上,我跟大貓坐在師大路公園石階上,我沒有精力吐出什麼臨別箴言,我們只是喝著沒氣的台灣啤酒,無味、像尿。
也不知道為什麼,我那時不僅覺得孤獨,也覺得生活之無意義與空虛,似乎一切事情只不過是包著保鮮膜的冷凍商品,在那塑膠表皮之下,什麼也沒有。
*
那天,大貓跟我說,師大路仍如同過去那樣永恆的絕望與虛無,三年前與三年後,大貓發現這裡的生活一成不變,有些人離開,有些人加入,但仍如黑洞般,師大路將同一票的年輕人吸附在公園大便草皮之上。這裡沒有未來,這裡只有小吃與啤酒和牛魔王,這是不是南村落,村落生產,但這裡什麼也沒有生產,而是有創意商品、研磨咖啡機、二手書的垃圾坑洞。
大貓跟我說兄弟,我們從裡到外都一起墮落發臭。
我們曾經一起在二十出頭的歲月裡踏在這大便公園裡,我們擁有這個世界,我們懷抱未來。
十年後我們卻都發現被一起困在這個地方,困在咖啡廳、the wall、夜市與大便草皮之中,十年前我們以為在這個地方有著一票奇形怪狀的年輕人,在台北南邊我們將有一片大事業,大場景,那個時候我們常常提“我們這個世代“,我們將如何如何地與前一代不同、而我們將前所未有。
最後發現除了大便草皮上的喝酒歲月之外一切仍找不著頭緒。
大貓說,師大路充滿了夢想家,充斥了大學生、失業分子、文青、知青、搖滾掛、電音掛,這裡是塑膠表面的生活。因為居住在這方圓不到十公里土地上的夢想家們以為只要有了態度、有了表象,就有了真正的文化生活。
你我知道師大路只是一種塑膠表面的生活,是消費生活。孤獨、虛無、與絕望也不過是名詞商品。你與我都知道,我們並不絕望,我們使用著父母的積蓄、生長於技術密集的出口型國家、在這裡失業不是失敗而是特權,我們都是天之驕子,絕望的年輕人只是布爾喬亞文青的罪惡感投射,自我解嘲。而我們這個世代最大的罪惡莫過於將自我解嘲當真而成為自我癱瘓。
大貓告訴我,兄弟,師大路是台北市最後的毒品,師大夜市內是毒品,師大夜市外也是毒品,夜市內是被千年塑化劑所毒害,讓人吃喝解決口慾、解決口腔,夜市外的草皮是另一個毒品,不賣珍珠奶茶賣生活方式,賣永恆的絕望與虛無、賣反叛也賣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