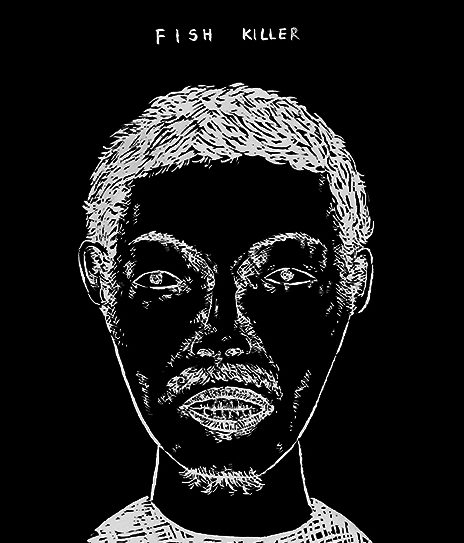紙張,為你記錄課堂寫下的連篇廢話;紙張撥開鼻毛,以螺旋身軀與鼻涕共舞;紙張下探股溝深處,與大便殘屑產生親密接觸。
但在某些時候,一張紙能夠改變你的命運。
2009年五月初,我接到一封英國寄來的信。
那是一張平凡無奇的A4影印紙,正上方是藝術學院的標章,一個盾牌、一隻老虎、與一本書。中間是洋洋灑灑的幾段文字,訴說著本人卓越的學術成就,樂觀開朗的性格,與活耀的社團活動,本系歡迎您加入我們!
當時的我,在夜半捧著哈電族電子辭典,以鉛筆圈寫著信中滿滿的生字,心中滿是無法抑制的亢奮感。
那封入學許可為我的人生劃分了一時間點,我所處的當下已過了有效期限,迎面而來的是嶄新的生鮮未來;我住的家,做的工作,身邊的朋友,家人,常去的餐廳,喜歡的城市角落,漫畫王,白鹿洞,五十嵐,都成為了過去。
我開始跟身邊的朋友聚餐,告別。朋友會拍著你的肩膀,說: 「保重」。
平常不是太熟的人會捎來短訊,說「珍重再見」。
身邊的親戚會包給你紅包,叫你好好上進,為國爭光。
之前合作過的雇主跟同事會給你花束,卡片,跟小蛋糕。
這一切,都代表了你已成為人際圈裡的過去式,一個人們會在聚會中提起的「喔那個人啊」, 然後又被遺忘的名詞。
但當時的我對此並不介意。我常耳戴隨身聽,無數次的循迴撥放著衝擊合唱團的「倫敦呼叫」,彷彿那未知城市正隔著歐亞大陸,傳來跨時空的呼喚。
那時的我儘管身處台灣,望眼所及卻盡是國界之外的美麗新世界: 那是個保守黨、英國國家黨、柴切爾夫人、布萊爾、莫里西、艾爾頓 強、史汀、大衛 鮑伊、足球狂、搖滾樂、與豆豆先生的土地.
2009年五月二十九日,我站在中正機場的航廈大廳。
那時的情景至今依然清晰,在腦海中像是電影畫面。馬英九剛執政一周,機場電視上滿是新總統就職的畫面;中正機場第一航廈內,新東陽店面前成排的肉乾發著油膩的光澤;我與父親坐在塑膠椅上,有一句沒一句的接著話。
「有帶護照嗎?」 我爸問我。
很有趣的是,在我人生無數次地出入境台灣,與我爸無數次地候機時刻,所有的對話,均以護照作為開場白。
「帶了。」
「水?」
「礦泉水過不了安檢,過關了再買。」
「錢有帶夠?」
「有。」
「台幣還是英鎊?」
「都有。」
「有帶些吃的?」
「有。」
「我這裡還有幾塊鳳梨酥,放在你包包裡,飛機上吃.」
就這樣,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鉅細靡遺的清點背包裡的每樣物品。
我爸是標準的台灣父親。這個男人在你兒童時期扮演著兒子大玩偶的角色,你記得在父親肩膀上的許多下午,你記得許多周末在圓山兒童樂園的周末,你記得他給你人生的第一台個人電腦,他帶你在國父紀念館溜直排輪等種種情景。
如同標準的台灣家庭關係,我的父子關係在情感上總是壓抑的,隨著兒童時期的結束,也結束了與父親的感情聯繫,剩下來的只是課業壓力,補習班,夜自習,期中考,大考,小考,與滿江紅的成績單。
一直到輕狂的青少年時期,父子關係便每況愈下,直達冰點,我與父親成為了同一個屋簷下彼此躲避、互看不順眼的室友。
最後,父親成為了家庭中的言語黑洞 – 在客廳盯著新聞喀水果、在餐廳翻報紙、在陽台條望遠方的沉默雕像。
直到某時某刻,必須對話的時間點,父子倆人才尷尬地四目相交,關心起護照等生活雜事。
在我走向海關之時,我母親正在研究機場慶祝端午節的大型龍舟,我父親在一旁幫我媽拍照並在嘴中碎念著。我在前面緩緩步行著,走入了關口,穿過玻璃門,腦中似乎想起了甚麼,於是回過了頭,我父母驚訝地發現我已經過了關,隔著玻璃看著我,於是兩人對我揮了揮手。我翹起大拇指跟小指示意到了目的地以後電話連絡。
隔著玻璃門,眼前父母的具有某種象徵意涵,代表了人生如機場閘口,可開啓也會關上,一旦跨過了一個時間點,一段人生便成為過去,永遠消逝,再也不會回來。
我把護照遞給一個臉很臭的海關小姐,她拿起那枚橡皮印章,敲擊在護照內頁時整個桌面都隨之震動,於是,我正式踏出了台灣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