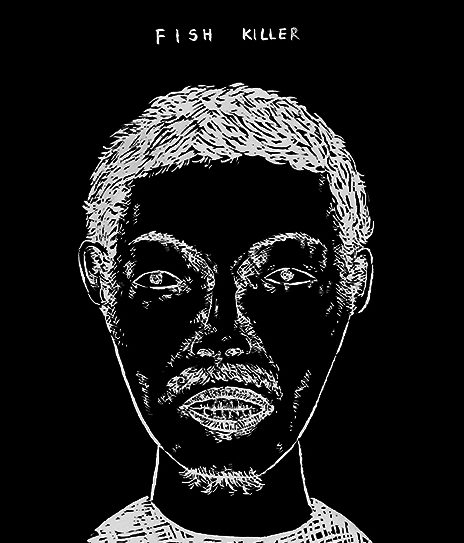我站在賽維爾中世紀小城的石子路上,眼前是漫無邊界的豔陽,地板在四十度的高溫中眼前的扭曲空氣,倫敦不斷陰雨的天氣似乎還躲在骨頭與身體的縫隙當中,我感到同時地酷熱與冰冷。
主座教堂裡的雕飾、那個一個又一個世代的穆斯林與基督徒、嘗試以相互競爭的宗教符號互相堆疊、仿佛征服這個建築、也征服了人類性靈的神殿,導遊指著穆斯林式天庭下的羅馬式條柱,穿插在穆斯林式神瓮下一尊又一尊的聖徒肖像,告訴我一個符號與一個符號之間、彼此相差百年之久.
當代人看到的時間,是在地鐵站上、抱怨著的兩分鐘誤點、與在電腦銀幕上出現、網路影片下載的百分比.相較於如此的毫秒世界.中世紀的歐洲人所看到的時間,是地球之於太陽的宏觀位置;相較於當代人走過博物館,斤斤計較地將眼前一切劃在藝術史年表:抽象表現主義(1940)、構成主義(1913-1920)、未來主義(1907),中世紀人看著周遭羅馬遺跡、穆斯林廣場、中世紀城堡,眼前所及不過是並存於同一個時空的混亂存在.過去的人悠游在千百年之間.而當代人則被困在歷史當中.
我走出大教堂、看到旁邊是一整排的紀念品店,賣著手飾、鑰匙圈、雕像等紀念品。作為一名觀光客,我真心熱愛著每個城市的紀念品店,不論你身在何處:北非或是南歐或是馬達加斯加,你只要把每個產品翻開、底下全寫著「中國製造」.工業生產的垃圾品不僅主導了人類生活、也殖民了想像力:人們將把這些沒用的手環、粗製濫造的皮包謹慎地包好、放在行李箱底層,帶到各自家裡的客廳,放著發爛,直到五年後的搬家再一口氣丟在垃圾桶裡。
在長達三個月的旅行當中,一種深深地荒謬感在心裡逐漸發酵。人們總是說旅行是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你必須在時在地、才能夠看到、理解這個世界。但是當你真的身處在當時當下之時,才發現世界之複雜、之荒謬,就如同人們說的「全球化」、每段旅行如同與其正面相望,面對其龐大之存在,身為一名人生的觀光客,如同以管窺天、只能以當下的片斷來理解眼前的現實,從表象世界的瞬間幻影來理解事物。
但是,如果以中世紀的方式、宏觀的角度來思考,所謂的「全球化」似乎是再簡單不過的事實:不論你身在何處,都將在下一家紀念品店買到中國製造的手環,而眼前的一切,不過是並存於同一個時空的混亂存在;人生的渡過,不過是地球繞著太陽運轉的星球位置.從巷子轉出、粉紅色月亮下賽維爾廣場閃著奇異的光芒,一群吉普賽媽媽圍繞著我、抓著我的手心,告訴我、我有個好心腸、將有一個美好的婚姻、並且多子多孫,並給了我她們手上的幸運草(當然是在我付了錢之後),那時的我想到了躲避佛朗哥政權、流亡多年的布牛爾,多年後的他回到賽維爾的同一個廣場拍攝人生最後一支片(That Obscure Object of Desire, 1977)時,他是否也感受到自己故鄉之超現實?他是不是也被同樣的吉普賽媽媽抓著手心,告訴他同樣的命運故事?
兩天後,我將搭機前往台灣,想到這個稱為故鄉的地方,竟也跟眼前的景觀一樣的陌生、一樣的難解.這是我旅程的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