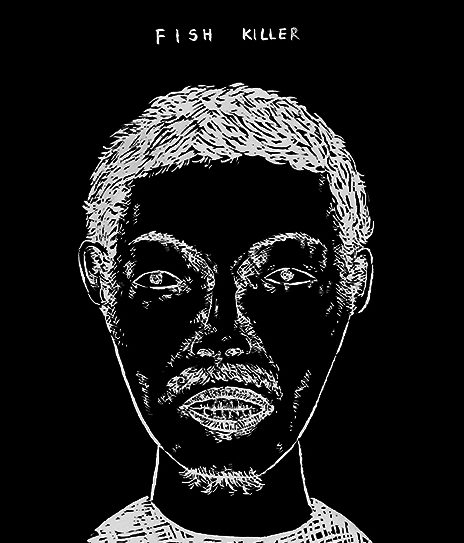Category Archives: 北京
地鐵
北京的地鐵跟台北捷運長很像,一樣的車廂結構,進了車廂以後大家要面對面坐, 觀賞彼此的面目可憎。 只是台北捷運很喜歡在關門前發出一連串急躁的鳥叫,鳥叫三十秒後關門。
台北的青少年總是在地鐵裡玩無聊遊戲,比如說在鳥叫的三十秒之內衝出車廂繞著車站柱子轉三圈最後在關門前夕衝進門。 在台北捷運,總是看到青少年一頭撞上已關上的車廂門的畫面。
在北京,每次在過地鐵的時候,必須經過檢查站, 你得把包包放過X光檢查機,並在另一頭取出,這道儀式總是讓我想到某種機械工廠。 每次我在過完檢查機時,總是打開包包裡的相機,檢查會穿透一切的X光在相機裡留下的東西。
第一次是一片白,裡面有很多孤魂野鬼。
第二次是一輛出租車,師傅正在毆打客人。
第三次是一隻貓熊。
第四次是一片黑,裡面有凶神惡煞。
北京泡泡
在北京浪花裡面第一個出現的樂團就是Joyside,主唱邊遠在鏡頭前說:我只想唱歌、喝酒、跟幹炮,在被問說為何的時候,主唱露出一臉疑惑的表情,我想他疑惑的不是對唱歌、喝酒跟幹炮而來,而是為何有人會質疑唱歌喝酒跟幹炮的權威性。
之後一個禮拜,我在一家胡同裡的酒吧裡看到邊遠,他如一片爛泥般倒在櫃台前不省人事,我給他一杯啤酒嘗試跟他說話,但他如爛泥般只是把啤酒一口喝而沈默無語著。
所以搖滾樂就是唱歌幹炮喝酒嗎?
如果你生在台北,北京是個迷思的產物,是口耳相傳、文章報導所見立的真實,而就算你現在踏在北京,迷思並未消除,只是不斷的增長,當我站在安門廣場時看著超大型動畫看板、各型各色的觀光客站在遠方的老毛肖像面前合照時,心中只覺得越來越迷惘。
搖滾樂、貧窮、四處借錢的生活也可以是迷思,而重點是,人們得靠迷思而活,後來跟李登輝見面的後一天,我遇到Go Go。 Go Go 說,這裡的音樂圈除了幾個上一代的大團之外,絕大部份的人都活在赤貧之下,雖然每週都有表演,但是中國人不喜歡買票,所以來的人絕大部份都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絕大部份的時候只在表演後半段來,等著拍手等吃飯,一張專輯不值錢,買的人少一出就等於滯銷,就算有人買了層層剝削下來大概幾頓飯就花個精光,人們玩搖滾樂,活在破胡同裡,沒錢買飯靠朋友接應,買酒買醉,靠著就是一種搖滾樂的迷思,人們不須要煙與酒精,人們只是需要煙與酒精所製造的迷霧。 這時候你可以聽到許多玩音樂的人會說:我為了夢想而活。
那麼究竟是夢想,或是一個迷思?
究竟是選擇生活,或是被生活選擇?
太空燈塔
李登輝在一進門後宣告今天的第一大新聞是在東北發現一種劇毒的蟲類叫做嶏蟲,此蟲含有劇毒,會痲痹中樞神經而致死,之後的一整晚李登輝便不斷地嶏蟲嶏蟲嶏蟲地說著。
當晚的後半段,他又開始不斷重複“一切都會更好“一句(不知從哪冒出來的)自言自語著。 李登輝是我在這認識的最奇怪的人之一,青島人,二十七歲,名字中跟台灣前總統音似的關係,而被稱為李登輝,原名已不可考。 李登輝原在青島地方電視台作播報員,可成為公務員領固定薪水並在地方過優渥生活,三年前辭職來到北京開始作劇場跟音樂,在別人家白住數年之後,現在終於在安定門與樂樂找到住處。
在問到為何辭職離家背井來到異處,李登輝說青島就如同文化沙漠一般,是給老年人度假的,不是給年輕人幹事的,呆在那會把腦袋呆壞,乾渴而死。到北京只是為了避免腦袋的死亡。 因為著各種原因,人們開始在都市與都市當中跳躍,從一開始的宣稱:這個城市爛透了,一個城市之賤比不上個體之志氣高昂,到下個城市尋找某個在這個城市失去的東西,又成為城市另一頭的某部份人的起點,北京青年開始離鄉背井,至全國四處工作。 在旅行的第五天,我發現在這個都市中漂浮著一票從各地聚集而來的人,在胡同中游走,為找尋知音、混口飯吃、呼吸空氣而活著。 也許觀看北京,已然不能從北京之中觀看,而是從那些流離失所的眼睛中觀看才能準確…
我想紀錄下這群人。
雙皮大媽
在南鑼鼓巷的滷肉飯店裡,老闆是老北京人,她說整條巷是她第一個作雙皮,後來整條巷子都開始作雙皮,之後她是滷肉飯第一人,而想而之整條巷子也開始作滷肉飯,她現在正在為領導巷子的下一波食品流行而煩惱著。
老闆說,北京人世世代代都很苦,如果你住在胡同裡,家裡沒廁所,半夜得穿戴整齊到巷口去上,唯一的好處是你代代都住在同一個城,同一個地方,祖先的城市。
老闆說現在北京已經是外省城,外省人從四面八方湧過來,擠爆了整個城市,擠爆了地下鐵、公交車,跟各種的交通系統,胡同開始一片一片的拆,外省人在北京四面八方建起了高樓,住的是有錢人,北京人買不起,外省人開始佔據各種城裡職位,北京人當不起,最後政府開始計畫性的把北京青年往外調,老闆說,被迫離開祖祖輩輩的地方往外省工作,有家歸不得,沒比這更悲涼的事情了。 老闆說的是身為北京土著的悲哀。關於被快捷酒店、文創古蹟、紫禁城中的星巴克的故事。
樂樂
在樂樂跟我說他就是所謂的”文盲”,他說他讀中學時因學校暴力事件退了學,從此開始四處打零工、賺錢,一直到前幾年接觸聲音,今年剛搬到北京,樂樂說他的人生冒險正在開始。
樂樂長得像我當兵時的同梯, 我的那同梯也是文盲,他說他也是讀初中時退學,之後便開始在中央山脈種果樹, 唯一的不同是,我的同梯在退伍之後又回到山上繼續種果樹的生活,而他畢生最愛的歌手是蔡依林。
一種北京的搖滾神話似乎仍在發生當中: 成千上萬的、所有全國各地的音樂青年離鄉背井,怀抱著夢想來此組團。 在台灣我這代的台北神話已經消失 ,在我這代,我周遭的朋友,從鄉下到台北是去廣告公司給人剝削, 直到筋疲力竭便去夜市買宵夜、看電影。
玩團的通常都是台北人,通常是公務人員家庭, 絕大部份的時間他們都在師大公園喝酒, 師大公園是全台北是最虛無的地方,它如同黑洞一般,進去了就在也出不來, 我曾有足足四年的光陰待在師大當中只是喝酒,再也做不了其他事情, 對我台灣的朋友,搖滾樂似乎不是那種遠大抱負的夢想,比較像是對抗與培養虛無感的工具。 這大概是北京音樂圈與台北音樂圈最大的不同吧,關於志氣過剩與中氣不足的故事。
三輪車
這事情關於來的第二天晚上我搭乘的人力三輪車,三輪車永遠出現在歐洲十九世紀拍的中國的相片,通常景色如下:胡同、泥巴地、和一堆車伕在三輪車前聊天。後來我發現車伕永遠都在聊天,似乎像是在百年前被詛咒般的不斷地聊天至現在一般。 很奇妙的是在人類發明了汽車、機踏車等各種瞬間移動器具之後,這個城市卻仍充滿了人力車。那天晚上因此我搭乘了三輪車,一路穿過後海,後來,車伕跟我收費七十塊人民幣,於是我們有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我說:媽的我搭出租車從機場開到市中心也不過五十你這擺明不是坑我嗎?
車伕說:這是北京的觀光特色。如同英法聯軍時在北京拍的第一張照片一般,三輪車因攝影術的發明,成為一符號、或是歷史的象徵,所以你搭乘的不僅是個交通工具,更像是一種時光機器,你穿梭了百年的時間,可以跟歷史、世界權力產生連結,殖民與後殖民、東方與西方、視覺現實與奇想,三輪車以它的物體性而扭曲了時光而產生間縫,人類發明了各種交通工具,並以更快的方式穿梭,時速、音速、超音速、光速、超光速、超超光速等等。但最後機器效率所造成的時間縮短已無法被客觀衡量,而一切都只是作為文化符號而成為一戀物癖。
我嘗試各種方式殺價,包括大吼、擺明沒錢、威脅要叫警察,但車伕無動於衷,在不想淪落到被一群車伕同業工會在路上圍毆的命運,最後我付了車錢。
低度開發的回憶在這裡是一種商品,而且是昂貴的那種。
花房姑娘
二零零二年那年冬天我在北京,那年的三里屯只有一條小街,
當年只有十九歲的我穿著一條垮褲,一路上的人都在笑我,人說,你怎麼穿著布袋在路上跑?
二零一零年我來到北京,現在的三里屯像是小時候玩的模擬城市, 遊戲裡面在資本主義發展至極致之後會有一種城中城的超級建築體,建築高大並戒衛森嚴, 可以讓中產階級市民、西方觀光客躲在裡面自給自足,並逃避外面流氓的報復。
在三里屯,人喝完酒就變成傻B,大聲吆喝並且像神功附體一般在高速車流中穿梭, 三里屯就是奇觀。
崔健在一無所有中的一首歌叫花房姑娘, 歌詞是如此地唱的: 你帶我走進你的花房, 我無法逃脫花的迷香, 我不知不覺忘記了,喔…方向。 北京城也在八年內成為一超級建築體,於是越近越看不見,越近越模糊,走進去了之後於是迷失了方向。